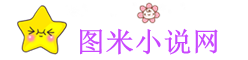准备出门时,笺素对上了坐在门口的已然过了七十岁大寿的婆婆的目光,心里不由掠过一丝不安。
果然婆婆又说起来了。
婆婆说,这样下去,迟早会遭报应,笺素不相信。
黄石公会发怒哦,婆婆天天这么念叨。可是,那间小小的神祠被推倒时,什么也没发生呢。笺素还特意跑去看,好不容易才进了工地里。那座神祠只是虚张声势地发出了巨大的轰鸣,甚至没能惊动附近旁观的两只通体乌黑的鸟儿。
传说中指点过留侯张良的黄石公,神力也不过如此啊。就像自家织的土布永远赶不上洋布一样,褪色的泥塑神灵也胜不过色彩亮丽的外来怪物呢。
啊,是了,丈夫说过,这怪物并不可怕,跟锄头斧子一样,是用来挖土、开山的。是英吉利的加克尔孙先生带来的。
听着丈夫这话,婆婆便又开始了。“跟着洋鬼子造孽呢……迟早会遭报应的……”
笺素就是不信。
洋鬼子,啊,不,是那位姓加的先生——应该是姓贾才对吧?但笺素没多问——丈夫去他那里干活,工钱从来不拖欠,当天就给发,是现钱。只是不怎么得空回家,但每天有人给村里留守的女人孩子带来消息和新崭崭的大洋。
“加先生是个善人呢!待伙计们好得紧,都说他比得上水泊梁山的宋公明呢。”带口信的人原是惯在酒店说书的,很有些见识,他都这样说,定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所以,笺素压根儿不怕报应。婆婆是年纪大了,老糊涂了。笺素虽则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可年纪还轻着呢!才不希望一直固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她早和丈夫讲好,攒够了钱,上城里去。
去做小生意去。
对啊,今天该是说书的那位到村里来的日子了。上次捎来的钱可还没动一个子儿。笺素牵念的也不是钱。
她要让那位带话过去,说老师夸赞大儿子很是聪明,有希望来年考上市里的学校。小女儿已经学会了用紫苏叶子煎蛋,嚷着要做给爸爸吃。她还想问,工地上干活是不是很辛苦,能不能挺得住;想打听打听,几时才能准假回来探亲。
这样想着,笺素走得飞快,不一会儿便看到村口那块大石头了。附近已然围了一圈人,都是各家年轻媳妇。
只是……她们脸上,怎么是那样悲伤的表情呢?啊,今年春天新嫁过来的那个水灵得全然不像山村姑娘的孩子,脸上亮晶晶的,是眼泪吗?她平时多么爱笑啊!现在,是在哭泣吗?
笺素几步挤了进去,被围在中间的说书人回过头来,向来活泼生动的面孔,此时显得如此僵硬悲哀。“是秦家的媳妇啊……请您节哀顺变……”
笺素眼前一黑,几欲倒下。不知是谁把她扶了一把,她愣愣地听着接下来的话。
“……今儿早上,三十六号人呐,就那样没了……”
距离文枞山不远的小城里。临街一家笺素所希望拥有的那种小铺子中,将一根辫子盘在头顶的店老板端上一碗河粉,同时对着客人半是不经意、半是刻意地说:“听说山区发生矿难了,费君姑娘可要去看看?”
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声音冷冷地回道:“山摧之难,非我等凡人之力所能相抗。”女孩子说罢,迫不及待似的,夹起一大筷子河粉,不顾烫地相当痛快地吸进嘴里,再开口时声音有了几分温度:“还有啊,不要叫我费君姑娘。君这个字,本来就是称谓了。再加上姑娘,未免太奇怪了。”
“费君姑娘说的是。”店主完全忽略了女孩语中的不满,笑盈盈地说自己的:“只是费君姑娘不是一向对这些事感兴趣么,大家都说是黄石公显灵呢,这不是费君姑娘的专业吗?”
“都说了不要乱叫,费君根本不是我的名字……而且,先不说跟黄石公有没有关系,发生矿难的话,应该是警察局的事吧?”女孩子依旧没什么兴趣的样子。
“警察局怎么会去管呢?这次矿主是洋人,讨好还来不及,怎么会去管呢?可惜了那三十几条人命。”讲到这里,店老板声音低沉了几分,“全是山村里头的人,被生生埋在下面了,似乎一个也没救出来。警察去了回来,就只给出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压根儿没提那洋人早给矿工上了险,给旷工家属的补偿不过是一毛之于九牛,也是山村里人没见识,居然也没有闹事儿的,还称道那洋人呢。那位如今可也没什么大损失呢。”
女孩脸上不复悠闲享受的表情,良久,道:“所谓‘华夷不可同居,人鬼岂容并域’,此话看来真有几分道理。”
“啊呀,费君是忍不下去了?不过这话是当年抵制洋教的檄文里头的吧,费君姑娘不是并不喜欢吗?——对了,听说那洋人也是基督徒呢。所以才完全不惧怕黄石公吧,把整座神祠彻底拆毁了,这种事都做的出来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费君姑娘?”
没有人接茬。
只是那只白瓷碗下,压着几张黄纸。人,已经走了。
店主往门外一瞅,又收回目光,苦笑着喃喃自语:“又是以物易物啊……这一次还是求财符……法篆还是自己刻的那方吗?也不知道究竟灵不灵验……”虽说是这样近乎抱怨的念叨着,店主还是小心地把它们折好,插进兜里。“嗯,可是这次要应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山妖树魅呀……”
笺素好容易哄睡了小女儿,静静坐着,凝神望着窗外。
一片漆黑。其实,应该是能看见大山的。半年前,即便是子时,也能隐约瞅见神祠的灯火,橙黄色,一闪一闪的,跟近处的萤火虫的青光辉映。
现在,什么也见不着了。连前些日子婆婆唠叨个不停的矿上的那有些刺目的白光也看不到。
说是“塌方”了。笺素不太懂。
“地崩山摧壮士死……”那天,说书人很是凄怆地说了这样一句文邹邹的话,倒是印在笺素心里。几天来做噩梦,梦境里皆是山石崩塌、天地失色的惨况,能听见丈夫呼救的声音,却没见到有谁伸出援手。加先生安安稳稳地立在一旁,只静静看着。到最后,瓦砾底下,没了声息……笺素就一下子惊醒了。
不会的,那个加先生,不是大善人吗?怎么会见死不救呢?一定是,无能为力吧。
是黄石公在报复啊。
婆婆说,这时候却没有往常愤愤的样子,只抹泪。“黄石公啊,不开眼啊,不去管管那洋鬼子,在平头老百姓身上撒什么气!”
笺素想劝,都开不了口。黄石公倘真有灵,也实在不长眼。可是,加先生到底也不算有什么罪过。也挨门挨户地赔了不是,又送钱又送白米鸡蛋的,大家伙收下,心里也有几分过意不去。总觉得加先生也不容易,听他说,是赔了本啦,但又觉得不该占工人的便宜,所以这补偿一定不能少。
没有男人做主,都是和笺素一样新寡的女子,至多,不过多了个老人,便是再要争,又能争来什么呢?而且加先生不过是一头红发、一双蓝眼珠子可怕些,说起官话来却是很地道,又是那样诚恳、那样动人的调子,甚至还掉眼泪了,感觉上是个好人没错,大家也就更没心争什么了。拿上了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几天来,家家基本上都下了葬。
唯有村头一家除外。棺材愣是停了好些天。也是昨儿,才办了丧事,还是村里人一起张罗的,因为前天晚上,又添了副棺材。现如今,这家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也是笺素唯一有点放不下的。
村头那家,男人死的早,只留了一个媳妇,拉扯着独子长大。今年那孩子才十六岁,十分乖巧懂事。又很孝顺寡母。心疼母亲辛苦操劳,前几年还小就成天上山打柴采药,补贴家用。加先生来后,这孩子听闻矿上条件好,挣钱又多,便不听劝地跟上了山。说是可算能让娘好好享福了。
那天说书人带来噩耗,受到打击最大的便是这孩子的娘。说什么也要找加先生算账。凭加先生怎样说也不听,还说,矿上压根儿没那样好。她的儿,小泉,在矿上是饥一顿饱一顿,干活儿却是不放松一点儿。在村里,见谁都这样说。
没几天加先生到村上来,听了这话,急了,说这是诬赖他,要讲证据。没成想这母亲真拿出一叠子信来。说书人方想起,小泉他娘是教书先生的女儿,小泉也识得几个字,每次不须说书人带话,自个儿写封信托他捎给他娘。但是小泉可是从没写过吃不饱饭的事儿啊!说书人当场拆了信,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念给大家伙听,都是在说“从没饿着”、“加先生救了大家伙儿”之类的。
那个格外阴沉的晚上,听着说书人念完信,小泉他娘语气很冷地说:“老徐,你是不懂,你念错了。”
“怎就不对了?”说书人觉得奇怪。
“老徐你呀,可是从右往左,竖行念下来的?”小泉他娘一笑,向来温婉的面孔,变得有些狰狞吓人。
“可不就是这样念么……”
说书人话到一半,打住了,看了眼加先生,又看了看小泉他娘。
“这是意外吧……”
加先生不明所以,举着灯一看,不知见到了什么,旋即抢过了信。他的脸色,也异常可怖。
“加先生怕是看出来了吧?倘若从左往右、横行念下去……”妇人的声音,变得凄婉而尖厉:“娘,我好饿!娘,救救我!——我的儿啊!你们这没人心失天良的鬼子,还我的儿啊!”
笺素和一旁围着看的村民,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手里还拿着加先生才给的钱呢。说书人回过神来好言劝大伙儿回去。
“刘婶儿是受了大刺激,大家多担待些,加先生自会安顿妥当的。”
听了这话也没谁好掺和,天色眼看晚了,谁家都有等着吃饭的孩子呢,也就回家去了,至多对小泉他娘安慰几句,可她又是哭,又是喊,什么也听不进去,大家渐渐也就都散了。
第二天一早,只见说书人悲戚地说,小泉他娘,昨儿明明好了些,加先生才放心回去了,没成想她还是想不开,竟是上吊了。
小泉母子两个下葬时,加先生哭得很悲。
笺素却没来由想起加先生那天晚上扭曲的面孔,心里一凉。
今晚,看着窗外一片漆黑,她觉着自己周围像也被漆黑笼罩似的。那个噩梦,还有……
原是不信婆婆的话的笺素,此刻也不由默念:黄石公啊,您老也开开眼吧,瞧瞧这山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这女孩子,年纪轻轻,来这样的小镇子做什么?
说书人本是在此等候加先生特地请来的方士的,看到这女孩子不由感到诧异,却是满脸挂笑,迎了上去。
“姑娘可是要去前头的镇子?——我可听说,那地方最近很有些邪乎,死了很多人。姑娘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还是不要去的好。”
女孩子却完全没有被唬住。她上下细细打量一番说书人,道:“您可是加克尔孙先生派来的人么?就是写信的那位徐相闻先生?”
“嗯?那,小姑娘你是……”
“我就是加克尔孙先生要请的人。”
“你就是费君?那个费君?”说书人露出惊讶的神色。他这才仔细看了看眼前的女孩。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样子,虽说穿着一身式样简单的交领道袍,腰间也像模像样的挂着似乎是宝剑葫芦之类的法器。但怎么说也跟传闻中善于驱邪祛妖的费君相去甚远。
看来,这次是失策了。加克尔孙先生几近崩溃地要求他去请捉鬼的方士来。说书人从城里消息最灵通的那位先生打听到这位费君恰好就在文枞山这一带时,他还以为这连日来的噩梦可算是能终结了。但眼前这过分年轻的女孩……
“我这几天在镇上也有所耳闻,加克尔孙先生的遭遇还真是令人同情。”女孩子倒没有在意说书人的不信任,径自向前走去,同时率先提起正事。“不过,虽说这镇上没有警察,可出了这么大的人命官司,城里的警察局也不管么?何况加克尔孙先生是基督徒,又怎么想到要请方士呢?难道是徐先生你出的主意?”
这女孩也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呢。说书人一时竟答不上来,犹豫了一下才开口:“虽说是警察局侦缉队长亲自督办的……可是还是没用。要说他们是给人害死的,看上去完全不像普通人能办到的事,所以,我才会想到是不是冤魂作祟……”说书人像是意识到自己说漏嘴,脸色一变,打住了。
“冤魂?啊,这么说来,镇上大家说的加克尔孙先生是因着推了神祠、遭黄石公报复,倒并不可信呢。我原本还担心黄老先生到底是位列仙班,不好对付。假如只是孤魂野鬼,可还容易些。”女孩虽是这么说,说书人感觉到她并没有丝毫放松的意味。相反,语气更凌厉了几分:“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冤魂呢?竟至于索了加克尔孙家三条人命?”
“啊,不,费君您忘了方才小人的口误就好。正如您所听到的,是黄石公显灵。固然不好对付,但事成之后报酬定不会少。”说书人匆忙解释道。
女孩似乎并不怎么相信。“真的吗?我还以为跟这附近村子那三十六条人命有什么关系呢——哦,不,听说新近又添了一条。三十七条人命。这事儿,那位侦缉队长可知道?说不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了,加克尔孙先生也就不必担心他那最小的孩子的安危了。”
说书人听得心惊,却强做笑容道:“费君说笑了,村子里头那是天灾,哪有什么冤魂之说?哪里要劳烦警察局了?跟加克尔孙先生更是没有什么关系。”
女孩子似是冷笑一声,不再言语。
两人一时无话,走了半里来路,说书人耐不住,讪讪道:“信里头也没说清楚,费君您既然来了,我便跟您说说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可好?也免得费君您受传言误导。”
女孩不应。说书人干咳一声,便径自讲起来。
“加克尔孙先生原是在文枞山开矿的,也是出于无奈才推了黄石公的神祠,并无不敬之意,原是打算事后重修的。后来发生矿难,加克尔孙先生为着补偿矿工家眷,一时没有余钱,才搁置了这事儿。现如今已经诚心悔过,只盼黄石公老人家原谅呢。唉,只可惜到底是耽搁了。
“先是大少爷和小姐,那天傍晚本是跟往常一样去园子里玩一会儿,哪成想才走出后门,便……唉,我早说那西洋的什么石雕本就不合适,那种大家伙,还挂在外墙上,说不准哪天就会掉下来。两个孩子当时眼看着就不行了,最后也没救过来……
“再说太太,就是孩子出事儿的第二天,太太原本一直在房里哭着。后来可算出了房门,就往园子里走,立在后门那儿看了一会儿,一回身就往一旁的柱子上撞。等我回过神来,去拉的时候,也已经迟了……
“侦缉队长说,孩子的事只是意外,太太大概是自杀。可是加克尔孙先生偏就不听。他心善得很,原本就因为黄石公的事感到过意不去,后来赶上矿难,家里又出了这档子事儿……”
“原来如此,这也真是叫人同情。”女孩子突兀地开口,重复道。接着又偏头看向说书人。“不过,您呢?原本也是那个村子里的人吧?来到镇上帮加克尔孙先生做事,却接二连三目睹惨剧,您——”
“我吗?”说书人别过头去,轻声说:“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帮佣罢了,有什么好说的。”
这座山总归是不太平了。
神祠若是还在,只消拿一百文钱,一双笔,一丸墨,恭恭敬敬地供给黄石公,或许还有救。但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
连一贯有主意的婆婆也这样说。
笺素自己倒是没什么,只不过,听人说加先生在镇上连遭不幸,才多事帮着打听。毕竟加先生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无端端死了妻子儿女,也委实可怜。
只不过婆婆都下了断语,想来黄石公也不会轻易原谅外来的加先生,山摧之难、至亲横死,大概也是出于警告,只能说,天意如此罢了……
但小泉母子二人呢?笺素虽尽力不去多想,还是放不下这事儿。或者加先生的确……
“呜哇——”
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笺素被一阵奇异的嘶叫声拉回现实,惊惶地看看四周。虽然自己一直小心谨慎地走在村人踏出的小径上,可也难免会碰见山猪甚至是孤狼。何况,这里已经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了,来的人也不多。要不是为了补贴家用,——笺素还不想动用丈夫留下的那笔钱——也不会走到这里来挖药草。
心神一定,她握紧了柴刀,站住不动,不敢发一点声音,心里默祷千万不要真叫她遇上什么。若是连她也倒下,这个家真就算垮了……
短暂的沉寂后又是“呜哇”一声。听上去就是从不远处那丛灌木后传来的。对方应该还没有发现自己,听声音也没有向这边逼近。总之,还是躲开为好。
笺素轻轻向后退半步,不料还是发出“喀嚓”一声。灌木丛叶片窸窣作响,显是有什么东西要蹦出来了。
笺素惊慌失色,掉头就跑,然而没几步便觉不对,感觉压根儿没东西追上来。回头一看。
根本不是什么猛兽。
小心翼翼从灌木丛中探出头来的,分明是几个孩子啊。
年岁不大,面黄肌瘦,看上去很是可怜。脸上好像还有泪珠子。这么一想,方才“呜哇”的声音,确实更像是人发出的哭声吧。
似乎也是觉得眼前的女子不像坏人,一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说:“那,那个……能……能帮帮我们吗?”
跟自家孩子差不了几岁,却这样瘦小可怜。笺素早已心软,温柔地问:“你们是哪家孩子啊?出什么事儿了啊?”这么问着,笺素心里暗想,这几个孩子面生的很,看上去不像村里人,别不是山那边的吧?若是这样,大概是迷路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去,流落在山里了吧?家里人大概急坏了呢。
“大,大哥他不行了……救救他,求您了!”
笺素一听,虽是惊讶,却也毫不含糊让这几个孩子领她去见那个大哥。几个小家伙却不像是迷路的样子,很是熟稔地带她穿过树林,到了一处……笺素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地方。
是工地吧。原先相当热闹的工地,现在完全被废弃了。能用的怪物似的机器也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破败的工棚——可以看出即便是完好的时候也相当简陋。
怎么会……加先生不是大善人么?
笺素正觉得迷惑,却瞧见了躺在树叶铺就的垫子上的瘦弱男孩。就是大哥吗?
救人要紧。笺素不待孩子们指引,边先行上前去探男孩的额头。然而她手伸出一半便止住了。压根不是头疼脑热之类的病症,这孩子消瘦程度较另几人更甚,根本,就是饿成这样了吧。
“大哥他……有什么东西只顾给我们吃,自己总说不饿……现在,起不来了,还不肯吃东西……”
另一个小孩子捧上一小把果子。“这些全要给大哥的,他就是不要。”
“就算吃这些,也不能……唉。”笺素叹一声,从包袱里摸出几个干馍。“就着水慢慢吃了吧,你们几个都是。再不济到山下村里头来啊,大家虽然都过得不容易,也不至于连这点事儿都帮衬不了。”
几个孩子不及道谢,先是给大哥喂起来。
只是听见笺素后半句话,他们纷纷变了脸色,露出恐惧的表情。“村,村里头?你,你是那个鬼子叫来的?”
“加先生?不是的,他早就去镇上了,不在村里。——你们认识加先生?你们是矿上做工的?他怎么如此待你们?”笺素隐约察觉到什么,不由反问。
“他向来这样待我们这些工人。别说吃一顿饱饭了,便是有饭吃,也是好的。”孩子们也开始吃起来,回答时也不那么生疏了。
“可是,他不是……他给的工钱,也不少啊?”
“您也是家里有人来矿上做工吗?怕不是也因为那天的事儿……”见笺素脸色变了,答话的孩子忙说:“我也不瞒您了,您怕是没用多少寄去的工钱吧?这姓加的给工钱,头几次倒是没什么,时间长了给的都是花不出去的假币。想我娘当初也是发现了这事儿,找上门来……可惜那天恰是这姓加的预备跑路的晚上,大伙都给下了药,睡得死死的,本是要被装车里送走的。偏生我那晚吃得少,睡得也浅,听见我娘的声音出去一看,那禽兽不如的家伙,竟然……狡辩哄不过我娘,就把她给……一枪……”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
笺素却顾不上去哄孩子。她怔怔地盯着破败的矿井。“加先生做的是什么买卖……”
“是……卖我们这些……小工。”似乎是吃了点东西有了力气,躺在树叶子上的男孩虚弱地开口道:“打着开矿的名头,哄我们上山来,随意挖几处修个矿井,骗着我们干一阵子活,还发给工钱。只是不许我们回家去。这样过上几个月,我们对这活计也上手了,他发给的工钱也慢慢全拿假币顶了,趁着家里人不及察觉,便带着我们去远处,立契卖给真正开矿的老板去。……我们几个,家离这儿远得很,早该被送走的。不过年纪又小,学得又快,动作也算利索,这姓加的就留我们几个,每次换了地方带带新上钩的矿工熟悉活计。没成想,这次出了这档子事……也亏他想得到,事先早办好了什么保险,那些人一死,还得了不少钱……您呀,别不是也给他骗了?这姓加的,才不是什么善人呢,根本就是,吸人血的……”
“吸人血的……加先……姓加的,当真如此?”笺素心下已是信了七八分,仍不愿全信。
“您就拿那钱,去集市上买些东西试试,不就知道真假了么?——咳咳!咳咳咳!呜哇——”男孩子猛然咳嗽起来,登时吐出一口鲜血,在黄土地上分外刺眼。
“大哥,你的病又……”
男孩勉力冲笺素一笑。“您瞧,若是真有什么好生活,我又怎会这样呢?我是没得救了,只希望他们几个……便是我们这次运气好没被埋住又有何用呢?如今家也是回不去了,只盼您能带他们到村里去……唯有一件事……万不可碰上加……咳咳……”
“我们也不走,不走!”几个孩子慌了,围上来都带着哭腔说。
“我明白了,明白了,这就去找他们算账去。可是,你们,都撑着啊,我们一起回村子里去,”笺素竭力忍着没跟着哭起来,却也还是抹了把眼泪,别过头说:“我……先去村里叫人来……”
一路疾走下山,笺素越发确信什么加先生压根不是善类。不然,怎会虐待那样的孩子?怎会那样紧逼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婆婆说的,真的是对的啊……难怪会遭报应呢,不是推倒神祠那般简单呀……
召集村人上山救人并不难。大家个个义愤填膺,气愤加先生的不义,更觉得几个孩子着实可怜,跟着笺素一起往山上工地走去。
但是,不对呀……笺素瞅着明显不一样了的小径直皱眉头。心里也越发不安了。有人,有人刚才来过了……
看到工地的那一刻,一群人竟一时发不出惊叫来。
这超出笺素的想象。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方才还咭咭呱呱说着话的孩子,都双目圆睁,浸在血泊之中。
“爸爸?爸爸!”
金发碧眼的孩童虽说着洋文,听发音与汉语却也一般无二。然而加克尔孙却不甚在意的样子,挥手示意仆人领孩子离开,只是盯着眼前的女孩,略带倨傲开口道:“阁下便是传闻中法术高强的费君吗?可有办法祛除妖邪,保我性命?”虽说是很流利的官话,听着却还是有些别扭。
女孩子目光从那被带出去的小孩身上移开,淡淡道:“法术高强倒不敢当,至于祛除妖邪之事还需酌情判断。”
“老徐想是已经跟你——跟您说过了。这两件事实在蹊跷,虽说警察也给出了解释,终究……”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间细微难明,出人所料本也很自然。”
“但是,这时间未免也太……”加克尔孙话到一半脸色陡然变得惨白,盯着房门。“动……动了……它它它动动动了……”
女孩也回过头一瞧,看那房门口挂着一串子灿灿的铜钱,正微微晃动,轻笑道:“这个也不妨,想是加克尔孙先生从别处得来的。只是您有所不知,这是所谓金钱剑,乃是道家法器。方士自可用它捉鬼降妖,您把它挂在这里可是没有半点用处的——我想也不会有哪位高人单留下法器却于驱邪无用,一看便是外行人巧取豪夺得来自以为是挂上的,又或者是江湖骗子拿这东西哄人骗钱,我说得可对?”
“啊,所以,您是说……这不是用来指明邪祟的?我原是以为……啊,是了,您说的不错,我是上了当了。”加克尔孙脸色好了几分,又道:“但我也确实觉得家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不是奇怪的声音,就是……总之,就是那个什么黄石公做的吧?费君可有法子对付?”
“对付黄石公自有专门的法子呢,您不必担心。可是,黄石公他老人家虽则脾气古怪,却不喜杀生,这怕是与您的情况不符合啊?”
“唉,大概是因为我并非你们同族,才会遭得此难。前两次是我妻儿替了我,可你们中国人不也有‘事不过三’一说吗?费君您一定要救我性命啊。石块坠落之类的我还能请保镖抵挡,可万一中邪触柱而死,便只是定个自杀,什么也得……查不出来,岂不冤枉?”
“哦,您的妻儿倒是死得其所呢。”
加克尔孙听着这话味道不对,可也不及细想,只接着拿出一只箱子。“事成之后,报酬定不会少。”
“报酬暂且不提。只是,加克尔孙先生,我自进屋以来,并未觉出分毫黄石公的仙气,倒是……”女孩脸色一沉,“听到山摧轰鸣、鬼哭之声啊!您说那石雕可不是被冤魂推下的吗?您的妻子可不是……”她看到面前男人的动作,只挑了挑眉,便打住了。
加克尔孙掏枪的动作极为利索。见女孩不再言语,冷冷地说:“您看出什么也不打紧,我也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害死我的妻儿。我只希望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请费君指点一二。”
“只保住您的性命,可也不难。只是令郎,还有这里的帮佣……”
“他们若是也给您报酬,我自然不介意您多助一人——我的孩子,自然时时跟我一处,保住我的性命也就是保住他的,还是说费君没有理解?”
“看到这个怎么着也会理解吧。”女孩虽是这么说,也没表露出半分怯意,只说:“不过,我想冤魂意在加克尔孙先生,也不必担心帮佣的安危。加克尔孙先生不若抛下一切家产仆人,只带着令郎,离开这里,我想冤魂也没能耐追上去。”
“一切家产?决计不能!”
“金银不过身外之物,与性命相比终究还是不及的。况且此事本就因钱而起,您又何必再对钱财恋恋不舍呢?”
“这……”加克尔孙面有豫色,对冤魂之说却不加反驳。
“想超度亡灵、化解灾厄,用钱是最容易的了……啊呀,您这是做什么?”
肩膀上还汩汩流着血,女孩却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平静地问。
加克尔孙面目狰狞。“你是假冒的?是那村里的人?原来是找我讹钱?你们怕是打错了算盘。我本以为你们见了那几个人的下场就会收了这种想法,你们以为警察会站在哪一边?”
“嗯?原来不单是那三十七个人啊。”女孩眸色愈沉,并没有理会加克尔孙的威胁,反是抽出几张符纸来。“那么要他们往生,恐怕更要费些精力了;既能造成山摧之难,说不定啊,还有纠缠已久力量惊人的怨灵,更不能小看了……”话语间似乎是要认真助加克尔孙了。
见了陌生的符纸,加克尔孙忙转而笑道:“方才是我一时冲动,等会儿便请老徐来给费君您包扎。费君出手肯定没有问题的,我抓来——啊,请来好几位方士都这样说,就是因为您姓费呀……”
女孩打断他:“您倒是很信任老徐,他不是仅是个帮佣吗?”
“诶?”加克尔孙不明所以,还是答道,“虽说是个帮佣,可也是我的助手,跟我的时间不长,但也是个可信的人,办事也难得的利落……这么说来,费君,还请您一并救了老徐性命。”
这请求依旧是用手枪要挟着提出的。
女孩也不以为忤,只说:“也只是小事。——您当真不顾妻儿如何丧命?”说着蹙眉偏头看了看房门。
“总归是鬼怪所为,又能怎样?若是有凶手,凭侦缉队长还查不出?把老徐来回审问了那么多次,最后还是说是意外、自杀。再要追查,也没有意义吧。”
“换言之,您只要性命……”
“还有我的全部财产,也不能损失分毫。”加克尔孙急急补充,“报酬虽然不会少,可是额外的花费我也绝不会接受的。”
女孩听罢,沉吟片刻,道:“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根除此患,第二步是在华厦作法……第一步,却是要您回到那山摧之地。”
迎着加克尔孙惊惧的目光,女孩一字一句地说:“您需得亲自超度那些冤魂。”
笺素没想到还能见到那个洋人。虽然他是戴了帽子遮了面孔,可还是给她认出来了。
但是真见到了,也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他。质问吗?讨要什么吗?他亏欠大家的的确太多了,但是……她也很害怕啊。生怕,会和那几个孩子一个下场。
所以只有装作没有注意到吧。
她跟同行的几人使个眼色,大家心照不宣地微微点点头,便佯作不知地往前走去。
“不必担心。您且收下这个。”笺素从那洋人一行人边经过时,却听见有人这样说一句。她略带惊愕地偏头一看,只见到一个年轻女孩的侧脸,肤色雪白,但还不及洋人那般,应该并非外族。她还未想清这女孩究竟是不是对自己发话,对方却一下握住她的手,旋即松开,便快步离去。
笺素待他们走远——看着是往山里去的——方看了看被塞进手里的东西。
黄色的纸,上面也不知弯弯曲曲画的什么东西,还盖了方章子,鲜红色,令笺素不由想到先前那几个孩子。婆婆这般见惯大风大浪的人,那日听了之后,竟也愀然失色。足见这洋人之残酷奸诈。
那姑娘与洋人同行,也不知是好是坏,平白递来的东西……
还是得去问问婆婆。——若是早些信了婆婆,大家想也不会收了假钱还拼命干活,更不会丢了性命。
到得家里。婆婆仍在惯坐的藤椅上靠着,见到笺素,含糊不清地哼了一声。
自那日几个孩子身死,婆婆精力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笺素轻叹一声,吩咐大儿子去帮着女儿生火煮饭——他自是无法念书了——自己先去将打的柴火摘的青菜放下,又倒了碗热水送来婆婆这边,同时将那几张黄纸拿出来。
“啊,素儿,你可算回来了。”婆婆这一句,此刻似甚有深意。她看着笺素好一会儿,目光方才移开,却一下钉在那几张黄纸上不动了。“这不是……费家的辟邪符么?素儿,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笺素见婆婆情绪激动,不由吃惊,但还是原原本本陈说了一番,暗忖,那姑娘大概送符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只是不知怎么跟洋人混在一起,怕是也受了骗了。
“唔,小姑娘啊。怎么会跟洋人一起?这也太折辱她费家的门风了。当真是少不更事。”婆婆摇头责备,转而又道:“不过,这辟邪符,倒是货真价实的。更何况,有她费家的法印。这许多符我们也用不上,素儿,你且分给村里人,教他们贴在门槛上。”
婆婆对这祭祀驱邪之事,向来见解颇多。笺素自然信服,答应着便出了门,临走时叮嘱两个孩子和老人先行吃饭,不必等她。
再回来时,婆婆已不在藤椅上了。
笺素便进了屋,桌上已摆好饭菜,看着是小女儿动手炒的,不由心下一宽。但很快想到大儿子失学,不禁叹气。终究是受了骗了,可怜丈夫也是……
两个孩子许是听见动静,欢叫着从里屋跑出来。女儿咭咭呱呱地讲自己怎样炒菜,儿子却在一旁,等着笺素吃完,方说:“太婆婆出去了。”
笺素急了:“出去?她去了哪里?天可眼看要黑了……”
“太婆婆说先别给娘说。她去山上了,本来说很快就回来的,可是现在也没有……”小女儿抢着解释,可说到最后脸上也显出担心之色。
“娘去找太婆婆,你们两个,乖乖在家等着。娘很快就回来。”笺素也觉得不对,简单安慰道,心里同样担心婆婆这么大年纪去山上究竟不安全。何况,洋人也是去了山里啊……
一心想着不能耽搁,笺素当即离了家,一路走得飞快,没多久便进了山。
凭直觉,笺素往工地上走去。
眼见着从这灌木穿过去便到了,笺素却听见似乎有人在工地上说话。她一时踟蹰不知该不该上前,登时感到衣袖被人揪住。
笺素回头一看,竟是婆婆。她正躲在树丛后,此时揪着笺素衣裳示意她蹲下,也不说话,甚是专注地透过树叶缝隙盯着工地。
笺素也学着看过去。工地上正是那个洋人一行人,除去洋人之外,还有那个年轻姑娘,一个七八岁的金发孩子,还有……还有那个说书人——现在他已被大家视为公敌了,村里的老宅早被拆掉。听说连他家祖坟也被糟蹋了。另外还有几个壮汉,牵着猪羊,抱着冥币,其中一人预备着生火。
“婆婆,这是……”
“素儿,你且看着。我倒看看这糊涂的姑娘怎样化解灾厄。真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婆婆声音似乎太大了,引得那个女孩往这边瞥了一眼。笺素心下紧张,不再说话,婆婆亦随之安静下来。
此时,工地那边人说话的声音格外清楚。
洋人先道:“费君要求的东西,我已置办齐全,接下来全凭您指示。”
女孩似乎便是他所提及的费君,应道:“自然。”随即,拈出几张黄纸,叠成三角,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贴在身上。
边上洋人似乎也想抢来几张,却终究没有动作。孩子嘻嘻哈哈自娱自乐,说书人则脸色木然不为所动。
女孩贴罢符纸,便接着命几个大汉宰杀猪羊。自己将冥币一张一张烧着,嘴唇翕动,似在念叨什么。
婆婆低声哼道:“倒还有点样子。”却见女孩似乎再次察觉,又看向这边,这次没有立即移开目光。反而像是真的见到笺素两人一般,直直盯着她们,口中仍念念有词。
婆婆便不再言语。
许久,猪羊血液已干,冥币亦已烧尽。女孩自腰间拔出长剑,凌空画了一个似圆非圆的图形,伴以一声大喝,便似失了力气似的,一手捂住肩膀,全仗一柄剑支持,勉强立稳,笑道:“好了,加克尔孙先生,如今你是不必担心了。”
笺素只觉得她笑容古怪。婆婆却在一旁直摇头。
洋人则是真心欢喜,问:“那么,这次可是永绝后患了?”
“当然。”
“那可多谢费君了。我本以为亲自超度有多难,原来不过是要我亲自去买来祭品……若是那位方士说的清楚,我又怎会夺他法器、伤他性命?哈哈……”洋人一时开心,竟至于口无遮拦。全然没发觉女孩神情改变,更注意不到婆婆早已怒容满面。
“您这样就够了。”女孩淡淡地说,打断了洋人愈加放肆的笑声。
“好,好。那么,费君,那个什么黄石公……”洋人像想起什么似的,又问。“应该也不用担心?”
“黄石公么……早就没有神力了,您自然不必记挂……”
女孩话音未落,婆婆已怒极,出声吼道:“放肆!”
然而笺素却不必担心给洋人发现了。因为与此同时,脚下的大地开始剧烈晃动,周围的山石也摇摇欲坠,工地中间,更是已被大块石头掩埋。
一时之间,笺素觉得自己仿佛回到那个做了千遍万遍的噩梦之中,神思恍惚,更顾不上自己和婆婆身处何地。
再次清醒过来时,婆婆还在身边。然而,整座山已经改变了面貌。
工地也彻底被毁。几个壮汉不见身影。而施法的女孩则半靠在一旁树根上,看上去也没受重伤,只是向着已经失去遮拦的笺素两人张望。看着倒无大碍。
笺素又向另一边看去,不由倒吸一口气。
洋人和金发的孩子倒在一处,身子却被巨石压住,两人都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断气。明明该高兴丈夫身死之仇得报啊……可是笺素完全不觉得喜悦。
还是说,因为说书人吗?
他并没有受伤,却伏在那块巨石上,放声痛哭。
入冬了。
整座山褪去了色彩,仅有新修的神祠光鲜亮丽,看上去格格不入。给人的感觉,倒有几分像半年前洋人开进山里的机器一般。
只是神祠香火再没有断过。大家都说,那天定是黄石公显灵,叫加克尔孙这个恶徒死于非命、断子绝孙。甚至有人说,那说书人后来投河自尽也是黄石公的旨意。他老人家其实看得分明呢。
况且,从重塑黄石公像之后,村子也渐渐安定下来。今年冬天,又是连降大雪。怎么看都是好兆头。
这天又是白雪纷飞。虽然庄稼人看着心里欢喜,终究不敢在这天气里进山去。
也只有费君姑娘才这样乱来呢……河粉店里,店主静静看向远方山影,不由想到。
此时,他牵念的女孩正在神祠前,悠然自得地踱步赏雪。只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并没有注意小径那边喀嚓喀嚓的轻响。待她一回头见到来人时,脸上自然而然流露出惊讶。
“没想到您真会赴约呢……我是很担心您拒绝的。”女孩微微笑着说道。
来人哼一声,道:“也是我小看了费长房的后人。虽然没有那驱使鬼神的符纸,可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啊。”
“那也未必。——不过确实,对黄石公您,我一介凡人也不好用强的。您愿意前来,我的确很高兴。这是不是表示,您同意——离开这位婆婆了呢?”
来人正是笺素的婆婆,村里颇有声望的老人。
听了女孩的话,她也并不反驳,只是说:“便是维持现状,也未尝不可。”
“啊,您是留恋人间的生活吗?”
“这家人也很不容易。”
女孩摇头,道:“笺素姐姐或许没有这样想过,但假如婆婆逝世,她会轻松一些的。”
老人叹一声:“当时我本不该这么做的。”
“您当时失了神祠,无处可去,恰好这位婆婆命不久矣,您暂且占据她的身体,也无可厚非。何况我听说,这位婆婆向来尊敬您,若是她泉下有知,也不会责怪于您。”
“她自然也不敢。她……”老人说完这句,似觉得不妥,便很快打住了。
“唉,只是您引发山摧之难,害了那三十六条人命,实在不妥。又牵连一位母亲悬梁自尽,几个孩子早早夭折,更有失神格啊。”女孩仍是摇头,“这洋人虽则可憎得紧,但他家破人亡,跟您也……”
山风顿起,老人背过身冷冷道:“小姑娘可别说这种话,不怕遭天谴吗?我既具神格,所作所为还不用你这凡人妄加评说。至于洋人的家破人亡云云,我更是闻所未闻,栽到我身上,真是奇哉怪也。”
“您这样说也没错,究其根本,这位先生终是不得善终的。但我总认为,纵然那位说书人才是我们凡人意义上的凶手,一切动机,还是跟那起矿难脱不了干系呢。”
“不过是他的贪婪不够彻底——居然还有一点未泯的良知。”
“真叫良知吗?帮着洋人榨取乡亲血汗并不感到不安,可是闹出人命却决定跟洋人划清界线。仗着洋人对自己的信任,推下石像砸死无辜的孩子,杀害痛失儿女的母亲,还精心伪装出意外、自杀的假像,对着警察面不改色地说谎,连自首的勇气也没有,更不曾向乡亲们道过歉——要说有什么功德,只有一项:他私藏的钱财数量之大,竟至于能修起这样气派的神祠。除此之外,他又做过什么呢?罪魁祸首也并非为他所除,看见昔日雇主死于非命,却真情流露大哭一场。我真看不出来良知呢。他只不过是个极度自私的可悲的人罢了。”
“是吗?我离开人世已久,对这些不大清楚了。”老人抚摩着神祠的柱子,木然道。
“您明明清楚的。您也是一样的吧。引发两次山摧,除去得罪您的人。这等手段,我们世俗之人再熟悉不过了。”
“这么说来,你果然还是要兴师问罪吗?真是……不自量力。”地上的积雪,似乎在微微颤动了。
“瞧您,不是又发怒了吗?认为凡人远不及自己,更不容权威受到挑战……所以,甚至不让那些亡灵安然往生,反而……驱使他们刺激村里人闹事,意图引来那洋人;甚至命他们缠着那位心理脆弱的说书人……就是希望,可以亲手除去加克尔孙吧?”
“所以,避邪符也是针对我?那天的仪式,也是为了带走那些鬼魂,削弱我的力量吗?你不去想法子驱除外夷,反倒想对我……”
“我是没有这个资格审判您的。您方才,已经为我解除了许多困惑了。逝者无法回来,纵然多么无辜也是枉然。只是您,就像我最开始说的,该回去了。”
费君直视老人混浊的双目,重复道:“请回吧,黄石公。”
“你,自以……”老人瞪大眼睛,四下细雪登时卷起,然而只一瞬,便飘然落下。老人眼里显露出几分惊恐、几分愕然,渐渐地失去了神采。这具身躯,亦慢慢倒下。
老人的声音还在回响:“……你自以为那就是真相吗?那个洋人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面临财政危机了,保险金可是不小的一笔钱啊,连我都知道……像我这种编制之外的神,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
“是吗……”女孩似乎这样呢喃了一句,却没有动容,一手持剑,当空一刺。
漫天飞雪中,隐隐能看见一缕轻烟,向着神祠飘去。不一会儿,神祠中原本略带呆滞意味的神像轻轻一震,显出一丝别样的光彩来。
整座大山,此刻显得分外肃穆安详,如有神佑。
仿佛从不曾显露出獠牙伤人一般。